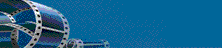北碚桅灯
文/李文山
夜幕沉沉。深秋萧瑟的寒风贴着川江江面拼命地咆哮,点亮世界的只余一星摇曳的灯火。
江水滔滔。一星灯火推出燃着的一盏煤油灯,出自美孚洋行出品的那种款式,安装在一条木质大帆船的桅杆上方,专供船老大夜间行船时照明使用。
灯火刺破沉沉夜幕,向着前方225°水平弧内发出不间断的白光。桅杆下方,站立着船老大江娃子。他身材着实,脸色黝黑,但还很年轻,大约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岁月沧桑掩不住他那眉宇间的勃勃生气。
“咳唷——咳唷——!”川江上水号子在航道艰险、水流湍急的江面上回荡,低沉而悲壮。
冰冷的秋雨中,一众纤夫着破衣烂裳,在险滩密布、礁石林立的江岸艰难爬行。
船到北碚码头,江娃子停船抛锚,把那盏桅杆上方的煤油桅灯取下来,提在手中,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前走。
目光闪回:三十五天前,还是在这个北碚码头,江涛拍岸,乌云压顶,近千艘各类船只云集,桅灯高悬照亮,大木船船帆林立,把宽阔的江面塞得满满当当,一眼望不到边。
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站在最高处,年约四十五岁左右,练就一副跑江湖的好身板,脸庞略显削瘦,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神,但眼眶布满了血丝,显然是过度熬夜所致。他就是民生轮船公司老板卢作孚。
一阵汽笛长鸣过后,卢作孚左手叉腰,右手挥动:“各位同胞,各位老大,如今南京失陷,武汉又相继失守,大量后撤到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十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国门已破,生灵涂炭,这些都是我赖以维系生存和坚持抗战的宝贝,我等不能坐视不管,任由倭寇宰割。我现在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名义,集中了我们民生轮船公司的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今天在此誓师,准备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抢运,恳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为国家保存一星余火。”
听罢卢作孚的动员演讲,码头上爆出一声怒吼:“我们跟定卢老板,誓死不当亡国奴!”
卢作孚双手一揖:“国家危难,我卢某就在此拜托各位了!”
汽笛再次长鸣,由二十二艘轮船打头,一声“开船了”鼎沸回荡,江面上一时万舟竞发。
江娃子也夹杂在数以千计的船夫之中。嘈杂的人声中,他不住地在向江边回望。
江边码头上,有一个少妇挥手的剪影。她挺着一个大肚子,显然是个身怀六甲的高危孕妇,嘴里似在大声喊着什么要紧的话。
有风呼啸吹过,绵绵雨点落下,江娃子的思绪折了回来。
煤油桅灯光影的折射下,看得见雨丝如麻,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一众纤夫已经散去。江娃子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雨水显然很凉。
北碚码头烟雨朦胧,灯光穿不透烟雨黑幕。在一团朦胧的光晕中,伫立着一大群年龄各异的女人。她们或披或执各式雨具,在风雨中死死盯着江面上的点点星火。
一个长相秀丽的年轻女子撑着一把油布雨伞在引颈探望。她叫碧云,是江娃子的妻子,脸色苍白,头缠白帕,一副产后贫血弱不经风的模样。
在碧云的视网膜中,只能看见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一瘸一拐,一盏美孚煤油桅灯在他的手中摇摇晃晃。
这个人就是江娃子。碧云的瞳孔一亮。
江娃子对迎出来的碧云说:“我是你的老倌,我回来了。”
碧云说:“我晓得你是我的江娃子,你的腿怎么啦?”
江娃子没有回答,盯着妻子的腹部反问:“你已经在家生下娃儿哪?是男是女?”
碧云说:“你走的第二天我就生下娃儿哪,是个蛮灵醒蛮标致的幺儿!你驾船出去了三十五天,我们的幺儿都有三十四天了。”
江娃子担心地问:“我不在你身边,生产时顺利吧?”
碧云说:“老天有眼,我生产时还算顺利,得亏隔壁的五婶帮忙接生,跑前跑后,可累坏人家哪!”
江娃子说:“这个人情容我以后再还。我回来了,就不愁还不起五婶的人情呀!”
碧云满脸愁云地说:“可是你的腿好像瘸了,今后拿啥子本钱还情哪?哦,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你的腿是怎么弄瘸的?”
江娃子说:“日本人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头上轰炸,我的腿就是被狗日的小鬼子给炸瘸的,弄得我现在没法再跟卢老板运货了。”
碧云说:“运不了货卢老板可以再想办法,最重要的是人能够安全回来。有老倌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
江娃子惊喜地反问:“真的?”
碧云点点头:“当然是真的。”
江娃子还在疑惑,碧云一把挽起他的手臂,极其勇敢地说:“走!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我们的幺儿。他很听话,现在正在家里睡觉呢!”
码头台阶上,碧云用右手搀扶着江娃子拾级而上,用左手打着伞为丈夫挡风遮雨。
江娃子右手提着的一盏美孚煤油桅灯照亮他们脚下的路,弯弯曲曲,起伏跌宕,坑坑洼洼,凹凸不平。
碧云深情地回忆道:“自从你三十五天前启程,驾着我们家的这只大帆船,跟了船王卢作孚卢老板,随同他的民生轮船公司,在川江三峡航段发疯般地穿梭抢运,我就望眼欲穿。生了娃儿还没有满月,我就天天在站在这川江边等你,到今天我已经等了第七个日子啦,好不容易才把你给盼回来了呀,我的老倌!”
江娃子说:“可你万万没有想到,你眼巴巴盼回来的是一个瘸子,既不中看,又不中用!”
碧云停下脚步,把右手从丈夫的胳肢窝抽出来,轻轻抚摸着江娃子的头,关切地说:“这三十五天我不在身边,你孤身在外冒着日本人的飞机轰炸闯荡,让你受苦了,腿瘸了不要紧,不是还有我吗?”
江娃子目光盯着妻子:“你可以做我的支撑!”
碧云坚定地回答:“当然,今后我就是你的支撑!”
一盏美孚煤油桅灯提在碧云的手中,一张简陋的大木床上,满月不久的幺儿在襁褓中熟睡,江娃子看了又看,然后忍不住亲了亲他的小脸蛋。
碧云笑了,笑出一脸幸福与满足。
江娃子抬起头茫然四顾,这是他们的家,一贫如洗。
碧云把桅灯挂在中堂前,要去给丈夫做饭。
江娃子却没有同意,他说了一声:“我不饿,只是身子怪累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吧?”
碧云贤惠地听着话,帮丈夫脱了外套,又三下五除二解除了自己的武装,钻进了被窝。
小别胜新婚。夫妻俩躺在幺儿的身边,恩恩爱爱地说着贴心话。
突然,江娃子转身伏在碧云的肩头,不像一个男人样哭天抹泪:“碧云,我对不住你和娃儿。实话告诉你吧,我的腿其实并没有真瘸……”
紧紧搂着丈夫的碧云一怔,瞬间松了手:“这么说,你撒谎骗了卢老板。国难当头,你怎么能当逃兵?”
江娃子说:“可我……我是太想你和娃儿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偷偷地跑回来呀。”
碧云说:“你晓不晓得自己是个孤儿,十八岁的时候跟定我父亲,才学会了在川江放船闯滩哪?”
江娃子眼含泪水说:“我怎么能忘记,是他老人家手把手教我闯滩运货,让我掌握了一身行船的绝技。从一般桡夫到一船驾长,我就是凭脸也能感觉到风的方向。”
碧云说:“不管是盛水暗礁还是枯水明滩,不管是黑暗急流还是浓雾浪高,只要感觉到风在人脸上移动,你就晓得船是否动了方向。”
江娃子说:“因此,别人不敢在夜间或浓雾中推渡,只有我敢。”
碧云也拭了一把泪:“后来我父亲在泄滩撞到了石坝之上,沉没江底再也没有起来,我也成了孤儿。”
江娃子说:“是老天爷让我娶了你,这是我今生的福气!我们成家后,也就开始了在川江上讨生活的艰辛。”
碧云说:“不想战争的炮火越来越近,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日本鬼子都快要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江娃子说:“你我都不晓得,军情是这样的危急。从武汉紧急撤出而拥挤在宜昌的近十万吨工业物资和三万多难民,急需撤往重庆,这些来自上海与武汉的工业设备关系到国家的命脉,按通常运力这些人和物需要一年才能运完,但是四十天后三峡就要面临枯水期,而同时日寇的军机正在加紧对川江狂轰滥炸,于是卢作孚卢老板临危受命,只得拟定了一个抢运计划。”
碧云问:“啥子抢运计划?”
江娃子回答说:“这个抢运计划,就是要把一年的任务抢在四十天内完成。他因此调动了由二十二艘轮船和紧急征调的八百五十多只木船组成的船队,冒着日本鬼子的炮火出征。”
碧云说:“北碚的青壮年都出川去打鬼子了,你也要去卢老板去抢运货物了。”
江娃子说:“离开家乡誓师出发的那天,我看见你挺着大肚子,对着我渐行渐远的我大声喊,江娃子,我等着你。我的心都碎了。”
碧云说:“你离开北碚码头的那一刹那间,我的心也碎了,可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丝自豪,为我有你这样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老倌而自豪!”
江娃子说:“我驾船抢运的这段日子,你在这所谓有西南大后方也过得并不平静啊,这教我在外面怎么不揪心呢!”
碧云说:“不仅是在我们北碚,整个重庆都处在煎熬之中,从川江方向传来的飞机的轰炸声,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自己还有亲人正在和鬼子进行着生死搏杀。”
江娃子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是卢老板说的。他说,只有我们替国家保存实力,赶走了倭寇,我们才能过上安生的好日子啊!”
碧云说:“卢老板说的对。江娃子,我在北碚还听说卢老板心地善良,要你们首先抢运那些孤苦伶仃的娃儿和民族工业仅存的那点元气,是真的吗?”
江娃子说:“当然是真的。卢老板交待我们说,娃儿是国家的未来,元气是抗战的急需。”
碧云大喊了一声:“江娃子,我的老倌!那你还回来干啥子呢?幺儿我给你养着,你还是回到川江上去搞抢运吧。北碚有那么多人都跟了卢老板的铁锚与罗盘,你为啥子要装瘸子偷跑回来呢?”
江娃子嗫嚅着:“我、我……我不是太想你和娃儿……”
碧云说:“你这是临阵脱逃,你懂不懂自己犯了啥子罪哟?”
江娃子还在犹豫:“我们抢运了二十七天,宜昌的江滩上还有那么多的货那么多的人,卢老板的中国敦刻尔克行动,要想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
碧云说:“越是不可能越是要努力。你现在就走吧,我和幺儿会一直在家等着你的。
江娃子说:“好的,我听你的话,明天——不,现在就回到江面上去,继续跟定卢老板搞抢运。”
北碚码头,晨光熹微。江娃子娴熟地起锚扬帆,碧云深情地递上那盏美孚煤油桅灯。
江娃子郑重接过挂在高大的桅杆之上,然后挥挥手,驾船驶向远方。
“咳唷——咳唷——!”一众纤夫唱着川江下水号子,声音高亢而嘹亮。
碧云泪眼婆娑,看着自己的老倌和桅灯消失在铺天盖地的川江烟雨中。
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船体支离破碎,桅灯眨眼熄灭。
北风凛冽。碧云伫立在江边码头上,一滴泪花从腮边悄然滑落。
一元复始的春夜,川江水碧如玉。
碧云手提一盏美孚煤油桅灯,怀抱一个幼小的男孩来到川江边,指着一个隆起的土堆对男孩说:“幺儿,躺在地底下的这个人是你的父亲!他和十六艘轮船一同被日本鬼子被炸沉,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民生轮船公司的一百多名员工。卢作孚卢老板说,他们是好样的,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
清明雨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川江之夜笼罩着薄薄的雾霭。
江岸、水波、植物与建筑都融在一起,绰绰约约。
那块凸显于江中激流的狭长巨石灵动起来,江水冲着它光滑的前额且不断撞出水花,听上去像历史在絮语不停……
这时候,一盏桅灯亮了,就亮在那块伸向江中的石头上,撕破川江上的重重迷雾,像一艘巨轮以中流砥柱的雄姿傲立江中。
这一刻,碧云看见了高举桅灯的是船王卢作孚,惊呼一声:“卢老板!”
狭长巨石幻化成卢作孚光滑的额头,和着漫天的水花一直撞击着粗糙的碚石。
“咳唷——咳唷——!”川江闯滩号子骤然响起,曲调粗犷而激越。
可是,一个幸存的女人还是看到了他,看到了那四十天的不眠之夜以及他眼里蛛网般的血丝,那些血丝是漫天的日本弹片划成的,跟自己的老倌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