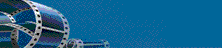神勇睿智的奶奶
——献给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文/桂斌
近来我时常梦见去世的奶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种愿望的自我满足与实现。可我究竟满足了什么?又实现了什么?这问题一时半会似乎难以说清道明。我和奶奶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两年,可我却对奶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一
家乡有一个怪怪的名儿——八斗碗村,这村名源自哪个年代,何故而得此名,没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后来有个风水先生不知是信口胡诌还是照葫芦画瓢地敷衍出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说法:该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其形状就像一只盛不完富贵的大碗,而环绕村子的山脉共有八座山峰,每座山峰的形状都像是倒扣着的漏斗,那漏斗能将四面八方的财气肥水纳入该村,故而得名八斗碗村,可算得上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了。如此说法听来就让人觉得玄乎、牵强。那年我随父母回老家探亲,听一个远房亲戚老人说过,年轻时他和那个邻村的风水先生还是拜把之交呢,两人常在一块喝酒行令。这就更让我置疑了,我印象中的风水先生应是洁身自好、清心寡欲、滴酒不沾的谦谦君子,怎可能是个酒肉穿肠过的凡夫俗子?我想那个所谓的风水先生八成是在骗得一顿酒足饭饱之后信口胡编出了那么一个哄人的说法。事实上八斗碗村一直都没有呈现过大富大贵的景象,也没出过大富大贵之人。
八斗碗村虽不大,但也不小,全村共有百十户人家。1921年,奶奶就出生在这个村子的一户殷实人家里。说是殷实人家,其实也不过就是祖上当年跑江湖做药材生意赚了些钱,又在家乡购置了几亩土地,日子过得比同村的一般人家稍宽裕一些罢了。不过.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姥爷在当地却是个响当当的侠义之士,曾姥爷年轻时练得一身好武功,他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恃强凌弱、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的地痞恶棍。遇有此类人事,他总会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一次曾姥爷到县里药行谈生意,那日是腊八节,县城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曾姥爷路过县城最喧哗的龙门街时,看到一群人正围作一团吵吵嚷嚷。曾姥爷挤进人群一看,不想这一看看得他七窍生烟怒火中烧,只见一个油头粉面的恶少正带着几个地痞流氓在纠缠一个十五六岁耍杂艺的小姑娘,恶少硬说小姑娘在他面前表演时偷走了他的一块镀金怀表,并强说那块怀表就藏在小女孩的裤裆处,因此他要对小姑娘强行搜身。尽管小女孩的爷爷在一旁苦苦哀求,甚至给那个恶少下跪磕头,求他放过小女孩一马,但那丧心病狂的恶少却一脚踹倒小女孩的爷爷,拽过女孩就要将手伸进她的下身。正在这当头,曾姥爷冲上前去给那恶少来了个叉裆扛甩,还没等围观的人闹清怎么回事,那恶少就结结实实地跌了个嘴啃泥。一旁的喽罗们见主子挨了这突如其来的一招,立刻围向曾姥爷,曾姥爷左右开弓,三下五除二就将几个地痞打趴在地了。曾姥爷拍拍手朝那恶少吐了口唾沫道:“这一老一少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明日我就揭了你的皮挂在城头上当鼓皮卖了。”吓得那恶少慌忙带着几个喽罗一瘸一拐地跑了。
从此曾姥爷声名远播,十里八乡提到他的名字没人不知晓不赞叹的。说到侠,曾姥爷还有更侠的事呢,老人家早年还参加过义和团运动,并从一个红毛军官手中缴获过一支双管短火枪。说曾姥爷义,那更是有口皆碑了,村里谁家有难他都会慷慨解囊,全村老少没有不夸曾姥爷人缘好的。
曾姥爷虽一世英名,却有一大憾事,膝下仅有我奶奶一个独女,且是他年近三十时才得了这么一个千金。曾姥姥生下奶奶后不久害了一场大病,虽捡回一条性命,却落下病根再也不能生育。奶奶长到五岁,便显露出了人见人夸的美人坯子,村里人见了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呶,仙女投胎你家啦!”“过不了几年,你家的门槛准让人给踏破啰!”曾姥爷的耳中塞满了此类的话语。见女儿出落得俊秀伶俐,曾姥爷心里喜滋滋的,他生怕亏待了闺女,特地从五里外的镇上请来一位私塾先生教女儿识字,初读些《三字经》、《女儿经》之类。只是有一事他很无奈,那便是缠足。山里女人与山外女人一样,世代沿袭裹足之风,五四运动都过去多少年了,但对女人的放足之风却没有吹进大山里。颇具见识、头脑开明的曾姥爷心里虽有疙瘩,却也难敌老伴的执拗,最终撂了句:“缠吧缠吧,只是害苦我闺女啦!”便到一旁抽闷烟去了,可怜的奶奶便在痛得死去活来中被缠了足。
“哟!那滋味可比死了还难受,三寸宽的布条缠你个三米长,我整整哭了三个月,声音没了,魂也没了。唉,遭罪啊……”我还清晰记得小时候奶奶指着她那双状如煮熟了的鸡爪一般的三寸金莲对我的诉说。三寸金莲缠成了,可奶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姥姥,却在那年春上老病复发撒手人寰。从此曾姥爷又当爹又当娘,一把米一勺汤,奶奶在渐渐淡忘丧母和缠足的疼痛中长大了,十五六岁便出落成了水灵秀气的黄花闺女。花好自然招蜂蝶,男人经过她身边都忍不住要用热辣辣的眼光瞅上她几眼,有更放胆的——南头村有名的乡绅赵八爷竟托人送来成匹成捆的绸缎和玉镯首饰。要给其羊癫疯儿子提亲。曾姥爷唬下脸冲来人道:“回去告诉你们八爷,桥归桥,道归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别瞎张罗。我家闺女不缺吃穿,不稀罕那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后来县里的一个保安团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也相中了奶奶,竟要纳奶奶为妾,气得曾姥爷差点带上那支双管火枪去找那个保安团副拼命。
不久抗战爆发,小日本逼近我家乡,兵荒马乱的年头,女人更多了一层担忧。曾姥爷生怕我奶奶遇有什么不测,成天护着奶奶,一听到村外有动静,他就带着奶奶到山里藏起来,这时他才平生第一次懊悔自己生的是女儿,要是男儿,一准早就将自己的武功传给他了。曾姥爷一肚子无奈,他盯着那支双管火枪琢磨开了:这小脚女人练拳脚不利索,可练打枪总该行吧?只要练出一手好枪法,防身就有了保证。曾姥爷一拍大腿:“行,就这么着。”于是曾姥爷开始教奶奶使枪,奶奶极有灵性,十天半月便能熟练地操枪使枪了,乐得曾姥爷逢人便说:“这闺女要是个带把的,一准比我强。”
枪练会了,可要遇到啥事三寸金莲的脚跑不开怎办?心眼活溜的曾姥爷上驴市挑选了一匹白唇白肚、背毛油亮、目光如炬、耳尖如兔的好驴。随后他又手把手地教奶奶骑着毛驴练枪法,正骑着练,反骑着练,平地里练,山上练,奶奶跟头没少栽,眼泪没少流。一年下来,奶奶还真的练成了一个能在驴背上灵巧射击的小脚女侠。奶奶后来正是依靠毛驴和双管火枪,在家乡演绎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随父亲回川南老家探亲。一天,我偶然从村里几个老人的交谈中听说了奶奶当年骑在毛驴背上用双管老洋枪打鬼子的事。我愕然不已,又将信将疑。我七岁那年,奶奶专程从苏南过来照看我、我和奶奶一起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印象中的奶奶是个走路颤颤巍巍、似乎一阵轻风就能将她吹倒的小脚老太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把她和属于男人的血与火的世界联系到一起。一个知了噪鸣的中午,奶奶在树下纳鞋底,我终于忍不住上前试探地问:“奶奶,听说当年您骑着毛驴用老洋枪打死过好几个鬼子,有这事吗?”奶奶停下手中的活儿抬起眼来,透过老花镜上方的间隙愣愣地望了我片刻后呵呵笑了,笑得很灿烂:“哪里听来的胡扯瞎掰,没那事,甭瞎听瞎问的,一边玩去吧。”
我愈发不明白了,倘若村里那些老人所说是真,那奶奶为何要对我瞒住这段经历?甚至她还可能瞒住了父亲,因为我从未听父亲讲过此事。是我听走了耳?抑或这事压根儿就属讹传?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后来我独自找到了村里满头白发的老村长,我想从他那里一定能弄清有关我奶奶的传说是否属实。听父亲说过,老村长当年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果然我一提起这事,老村长就如同麻袋倒核桃般哗啦啦地对我抖落了个底,奶奶在我心目中顿时成了半人半神的奇女子。至于奶奶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之谜,我在二十多年后才最终得以解开——
1939年底,侵华日军山地作战专家、被日军吹捧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命丧我八路军的炮火之下。日寇疯了似地对我苏南根据地采取野蛮的扫荡报复。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军民坚壁清野,避实就虚,有效地抗击了日寇的疯狂扫荡。老村长那时带领村里的民兵用自制土枪、石雷与日寇展开斗争,奶奶因为会骑着毛驴使枪,又练就了一身胆识,被选为村妇救会主任。别看这妇救会主任平日里只是带着媳妇姑娘们纳鞋织布,关键时候也得挺身而出,不久,老村长造土地雷的火药用完了,得有人到县里搞来硫磺和火药,这可是随时都可能脑袋搬家的事,日寇对硫磺火药看得紧,不是轻易能弄到手的。“这事交给我!”奶奶对老村长撂下这句话后就迈着颤颤的小脚走了。一顿饭工夫奶奶就上路了,只见她红袄加身,黑裤束踝,骑在毛驴背上一颠一颤悠哉游哉,一副走娘家的媳妇模样。
后半晌进了县城,奶奶落落大方地进了一家药铺,掌柜的一见奶奶,连忙让小伙计将准备好的货悄悄塞进毛驴背上的布袋里。临了还送到门外笑吟吟地交代一句:“大小姐走好,上花轿那天可别忘了用我家上好的货蒸一锅白面馍,让我们也好放开肚皮吃个爽啊!”这话是给周遭的那些暗中眼和隔墙耳听的。曾姥爷凭着他多年与老药行的关系以及他极好的人缘,早把事情安排妥了,本以为一路顺风顺水的,可偏偏遇上了风浪,奶奶的毛驴悠悠晃晃往回走了两个时辰,眼看就要到家了,这时奶奶身后传来一阵突突的马达声。驴背上的奶奶扭身一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只见身后数十米远的公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日军三轮摩托正朝她疾驶而来。边斗里的鬼子手握着歪把子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奶奶。坐在后头的鬼子肩扛长枪,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发出冷冷的寒光,枪刺上还挂着一面日本膏药旗。奶奶毕竟遗传了曾姥爷的血脉,她很快镇定下来。心想,自己四条腿的肉驴子肯定跑不过小鬼子三个轮子的电驴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老娘不走了,等着你们来。今儿个就是死也要拉上你们垫底。于是她立马吆喝驴子停下来。
“喂,花姑娘,你的什么的干活,驴子驮什么东西?”奶奶刚停下,那突突的马达声就伴随着鬼子的吆喝到了跟前。
“太君,本姑娘是八斗碗村的良民”,奶奶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晌午回了趟娘家,这会儿正赶回公爹家去呢,顺便捎了点玉米面”。
鬼子们见奶奶如花似玉,落落大方,早已筋酥骨软。边斗上的鬼子兵与后座上的鬼子兵相互瞅了瞅,两人脸上立马露出了淫笑。“啊啊花姑娘,八斗碗村的良民大大的好”,边斗上的鬼子放下手中的机枪从车上跳下,“花姑娘良民的也要检查检查的”。后座上的鬼子兵也追不及待地跳下车,将枪往摩托斗上一靠,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奶奶的胸。
眼见两个鬼子兵挨近了自己,奶奶没有慌乱,仍是笑吟吟地:“那太君是先检查驴子还是先检查人呢?”
“啊哈,花姑娘大大的配合,那就先检查人吧!”机枪手淫笑着对同伴道。
“先检查花姑娘的大大的好。”另一个鬼子咽着口水应和。
“那好,本姑娘就让太君们好好见识见识吧!”说着奶奶主动解开了红棉袄上襟的布扣,鬼子兵瞅见奶奶雪白的脖颈和红红的肚兜时,傻眼木愣了。趁着鬼子兵意乱神迷,奶奶猛地从怀里掏出上了膛的双管枪,随着砰砰两声枪响和两股白烟冲腾而出,两个鬼子兵木桩一般栽倒在了地上。那个开摩托的鬼子被眼前的情形吓傻了,他张大着嘴,惊恐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奶奶手中仍在冒烟的枪口,片刻后他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猛地加大油门一溜烟跑了。望着摩托扬起的尘烟,奶奶持枪的手无力地耷拉下来,奶奶的双管短枪里只有两颗子弹。倘若最后那个鬼子兵没有被吓懵,后果不堪设想。
奶奶只身击毙两个鬼子的事立时传遍全县。添油加醋者竞把奶奶描绘成一个红衣精灵,说当时鬼子的摩托忽遇一阵狂风,把鬼子兵吹得睁不开眼,狂风过后,只见一美貌的红衣女子骑着一头神驴从天而至,还没等鬼子兵回过神来,那红衣女子便轻抛酥手,两道红光闪过,两个鬼子立刻毙命。随即那神驴驮着红衣女子连奔带飞,眨眼工夫无影无踪……传说归传说,这事却惊动了驻扎在县城的日军队长片山大佐,他摔碎了一只青瓷茶杯后说,既使将整个大山搜一遍,也要除掉这个女共党。奶奶料到鬼子会报复,她找到老村长和几个村干部紧急商议对策,于是一套对付鬼子的办法就从奶奶的口中有板有眼地兜到了桌面上。
不出奶奶所料,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村外山上了望哨旁的消息树突然倒下,这是鬼子要进村的紧急信号。村妇救会干部与村干部一道带领乡亲们往村外一处隐蔽的山谷里转移,老村长则带着民兵们上了村外的虎嘴崖设伏。虎嘴崖是个险峻之地,一条羊肠小道逶迤通向山顶,山腰有一道形状像老虎嘴的险关,仅有不到半米宽的崖道,且有些向外倾斜,人要猫腰才能勉强通过,稍有不慎就会滑下山崖摔得粉身碎骨。乡亲们都转移了,奶奶却一身红袄黑裤骑着毛驴在村口溜达,毛驴后背还驮着两只木桶。少顷,当奶奶看见离村口不远的公路上扬起尘土时,她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抽出双管短枪朝天砰砰两枪,然后用小柳条轻轻地抽了一下毛驴的屁股,毛驴像知道奶奶心事似的,得溜溜地一路往虎嘴崖方向小跑而去。已经挨近村子的鬼子们听到枪响后立刻循声追过来,为首的正是片山大佐,他见山道上骑毛驴的红衣女子,便挥舞着马刀声嘶力竭道:“快给我追上去,抓活的,我要亲手把她剁成肉泥!”鬼子兵沿着山道朝我奶奶追,奶奶不急不慢地与鬼子兵保持着一定距离。挨近虎嘴崖时,奶奶下到地上,老村长从虎嘴崖那边过来接应奶奶,他将两只木桶卸下,帮着奶奶和毛驴过了虎嘴崖。随后他打开两只桶盖。一边小心地往虎嘴崖那边后退,一边将桶里的桐油倒在险要的崖路上。刚布设停当,鬼子兵就追了上来,走在头里的几个鬼子抓奶奶心切,叽哩哇啦地喊叫着逼近了崖口,当他们穿着大皮靴的脚刚刚挨上虎嘴崖狭小的路面,就哗啦啦地滑坠下山崖稀里糊涂地断送了小命。后面的鬼子发现有诈,立马收住脚不再贸然前行。片山赶上来,他观察了一会.便命令几个士兵脱下军装铺在滑溜溜的崖面上,随即指挥部队继续过崖。十几个鬼子战战兢兢地刚通过虎嘴崖,忽然轰轰几声巨响,惊魂未定的鬼子兵被老村长和民兵们预先埋设的地雷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急火攻心的片山丢下几具鬼子的尸体,挥了挥手下令部队撤回。
片山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会栽在一个黄毛丫头手上,半个多月他才从恼羞气急中渐渐恢复过来,他发誓要洗雪耻辱。片山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是个专事研究山地作战的老手,他想出了一招所谓的“以夷治夷,以诈取胜”的计策,找来县伪军大队长裘世荣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了一番。
三
初秋的一个黄昏,夕阳把最后一道金光抹在山梁,阵阵略带寒意的秋风将山野吹刮得一片萧瑟。奶奶正在收拾晾晒的大枣,蓦地,拴在墙角的毛驴开始一个劲地蹶蹄子,且竖起鬃毛,鼻孔里还不停地往外喷粗气。奶奶起初以为是驴子使性子或是哪儿不舒畅,便上前摩挲抚慰一番,可驴子却朝奶奶又是蹶蹄又是甩尾,一阵莫名的不祥之感突然袭上奶奶心头。这时一名村儿童团小岗哨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奶奶:村外路口来了五个身穿便衣、骑着毛驴的汉子,为首的那个声称他们是八路军军分区敌工部派来执行特别任务的小分队,说是要见村干部或是妇救会干部,这会他们正被另外两名儿童团小岗哨缠在村外路口。奶奶一听心里倒腾开了:不对呀,甭说军分区,就是县大队或区小队平时派人来,也得事先由交通员联络妥当才成,看来这些人来者不善,难怪毛驴直蹶蹄呢!
奶奶拍拍小岗哨的脑袋说:“快去通知老村长,让他带着民兵操家伙立马赶到我这儿,然后你再回到村口去把那拨人带到我家来。记住,要尽量拖住他们,这样我们准备的时间就更足。
小岗哨一溜烟地跑了。半支烟工夫,老村长就带着二十几个民兵赶来了,奶奶撂下一句“待会儿听我的吆喝再动手”,随即她三下五除二地指点大家在驴棚草垛以及房前屋后的草丛里设好埋伏。刚准备完毕,院子外面就传来了驴子的嘶鸣,一拨驴队进了院子。奶奶笑吟吟地迎了上去,不等来人开口,奶奶便自我介绍:“我叫兰玉彩,是村妇救会主任,请问你们是……”
“我们是军分区敌工部的,杨司令特派我们来布置重要任务。”为首的掏出介绍信递给奶奶,奶奶接过介绍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我区敌工部刘天光等五位同志前往你村联络有关事宜,请予接洽。下面是军分区杨司令的亲笔签名。奶奶念过私塾,肚里有一点墨水,她稍稍细看了几眼便看出了破绽,介绍信上杨司令员的签名是伪造的,因为奶奶曾多次从联络员手中见过杨司令员的亲笔签名。再说这张介绍信的纸厚而亮,与先前联络员使用的那种粗糙且有些发黄的介绍信纸质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奶奶仍表现出一副热情好客的神态:“哟,是军分区派来的呀,欢迎欢迎。”话音刚落,一只才进院的驴子不知是被奶奶的毛驴吓着了还是怎的,拉出一泡屎来。奶奶低头一瞧,只见那驴屎呈浅黄色且光滑细腻,没有一丝杂草茅根的影儿,奶奶心里更有了几分明白,这牲口吃的准是粮食,而老乡家和我们队伍上的牲口是吃不上粮食的。心谱愈发清晰,奶奶也就愈发从容淡定,她不动声色地将来人请进屋里。
“炕上坐吧!”奶奶将一盆大枣搁在炕上的矮桌上,然后慢悠悠地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为首的朝屋子四周打量了一下,也脱鞋上了炕,其余几个散开在屋子里蹲下,贼溜溜的眼睛却四处转悠。这时眼尖的奶奶又瞅穿了那为首的袜子不是我们队伍上的,准是日本货。嘿嘿,犊子露尾巴啦!奶奶心下思忖道,面上却笑问道:“各位来村里定是有要紧事吧?”“啊啊,是的是的,烦劳兰主任通知村干部和民兵队长都来开会,人到齐了我们就说正事。”
奶奶心想,王八犊子好毒啊,还想一网打尽,老娘先一锅端了你们。想到这,奶奶伸抓起一把枣递给为首的,“来来,尝尝我们村的枣,甜着呢!”为首的伸出双手接过枣,奶奶又将手伸进盆里,这回她不是去抓枣,而是飞快地从盆底抽出了那支双管火枪,刹那间,两孔并列着的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为首的头。“犊子们,我叫你们来得了回不去,都别动,谁敢乱动就崩了谁。”奶奶大声喝道。
一伙人还未反应过来,老村长就带着民兵冲进来,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五支日本造的手枪和几枚柠檬手雷,以裘世荣为首的五名汉奸偷袭队被一网打尽。
老村长和民兵们抓起刚缴来的油黑发亮的手枪,翻来覆去地瞅着掂着摸着,老村长将一支伸到奶奶面前:“小兰子,这回胜利你功劳最大,我看你就揣上一支小鬼子的新货色,把你爹给你的那支老掉牙的枪换了吧?”
奶奶盯着老村长笑而不答,也不接枪,半晌。奶奶才意味深长地对老村长笑道:“说我功劳大可不敢当,打鬼子除汉奸光靠我一个小女子能成啥气候?还得靠大伙拧成一股绳。说到枪啊,我还是喜欢我这老伙计,使惯了顺手呢。倒是你们民兵队的那些土枪该换换了。”
老村长正要往下说时,奶奶截住了他的话头:“不过这事可不那么简单,你知道队伍上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再说眼下前方的八路军许多带兵打仗的都还没一支像样的枪呢,我看我们还是先把这些枪交给队伍上吧!”
老村长一听,眼睛瞪得牛蛋似的:“那我们还打不打鬼子啦?老用手里的这些破玩艺儿能把鬼子赶跑啊?”
奶奶面带微笑地对老村长说:“你可真是炉灶头上的鞭炮——刚遇点热就要炸锅,亏你还是七尺男儿,怎就那么点能耐。我们这次把枪给了队伍上就不会再向鬼子要啊?”
老村长嘟起嘴,半晌才蹦出一句:“这事你当磕巴一只核桃那么容易呀?”
“那也不见得有上九天摘蟠桃下东海摸龙珠那般难吧?”奶奶依旧笑呵呵地,“咱就不会动动脑筋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还合成一个诸葛亮呢!”说着奶奶颠着小脚走到老村长跟前,凑近他耳根嘀咕了几句,老村长的脸顿时就像三月里的春花一般笑了:“兰子妹,还是你行,你要是个男儿身哪,在队伍上当个团长包准不成问题。”
“瞧你说的,我哪有那么神?还不是靠大伙呗!”
那场兵不血刃的战斗过后没几天,五支崭新的手枪就送到了八路军军分区首长们的面前,军分区杨司令员听说了奶奶和村里民兵们与鬼子斗智斗勇的事迹后,高兴得连声称奶奶为奇女子。他还专门请一个八路军战地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奶奶与小鬼子斗争的故事登在报纸上,奶奶立时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其名声比我的曾姥爷是有过之而不及。
片山大佐“以夷治夷”的计策失败后,村里召开了有村干部和部分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对几名汉奸的处理问题,许多人主张将抓获的裘世荣等五名汉奸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对这些良心烂透的家伙就得杀一做百,看看谁还敢当小鬼子的巴儿狗。”“对!杀了这些败类。”
老村长事先听了奶奶的一席悄悄话,心中自然有数,待大伙的意见提足了,他开口说话了:“照理说,让这几个帮日本人干尽坏事的狗汉奸吃一百个枪子也不为过,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讲求优……优……优个啥来着?哎,兰子妹,我说不明白,还是你来说吧!”
老村长面红语塞,奶奶扑哧笑了,“共产党八路军讲究优待俘虏,只要今后他们不再帮小鬼子欺负自己同胞,且有立功赎罪表现.我们就给他一条活路。”
奶奶话音刚落,一旁耷拉着脑袋的裘世荣便扑通地跪在了奶奶跟前,“我的好姑奶奶,从今儿起我们弟兄几个绝对听从八路调遣,争取戴罪立功重新做人,如有二心愿遭天打五雷劈……”
“你们要敢生二心啊,不用天打五雷劈。量你们也躲不过我这管老杆子。”奶奶拍了拍腰间的短枪说。
“是,是。”裘世荣连磕两个响头。
望着裘世荣,奶奶俊俏的脸上呈现出少见的威严:“起来吧,你若还是个中国爷们,明日就挺起脊梁跟我们走一遭。”
“好,好。”裘世荣抖抖瑟瑟地站了起来。
四
次日天麻麻亮,驴队就悄无声息地出了八斗碗村。走在头里的是我奶奶,奶奶仍是红袄黑裤,一副俊亮模样,只是奶奶身上被五花大绑着,跟在她后头的是头戴礼帽、身着白色绸衣、下着黑灯笼裤的裘世荣,紧挨着裘世荣的是老村长,随后是十几个民兵。老村长和民兵们的穿着也和裘世荣差不离,乍看上去怪怪的。驴队出村后便沿着河边小路逶迤而行。
驴队走了将近一个时辰,太阳才从东方天边露出了小半个脸,爽爽的风迎面吹来,带来了阵阵大秋作物的甜香味。几只红嘴鸦在陡峭的黄土崖上叫唤个不停,骑在毛驴背上反剪着双手的奶奶心里琢磨着:今儿这光景一定是个好兆头。她不时拿眼角瞥一眼老村长,见他的一只手总是时刻不离地紧拉着裘世荣的衣襟。原来为了预防裘世荣使诈,奶奶和老村长想出了一招,将两颗缴获的柠檬手雷挂在裘世荣腰间,并将一根细绳的一头拴在手雷的拉环上,另一头穿过裘世荣的衣袖拽在老村长手中。这样一来,裘世荣有啥心眼也不敢轻举妄动。驴队一行人转出了山坳小路来到了公路上,前面离鬼子的炮楼不远了,已经能够隐约瞅见远处炮楼的影子。又走了近两里路,一行人终于挨近了炮楼,炮楼前横亘着一道约两米宽一米多深的防护沟,一扇厚厚的吊桥斜刺里吊立着,严严实实地挡住了通往炮楼的路。
“裘世荣,你听好”,奶奶压低声音警告裘世荣,“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依我们的眼神行事,甭想耍花招,别忘了你腰上的有两颗核桃果子,赎罪还是找死你,自个儿定夺好了。”
“一定将功赎罪,一定将功赎罪。”裘世荣连连点着脑袋道。
这时炮楼吊桥前站岗的鬼子喊道:“喂,站住。你们什么人的干活?”鬼子兵一边大声嚷着,一边举起手中的枪对准了奶奶这边。老村长立马给裘世荣使了个眼色,裘世荣扯开嗓门朝鬼子哨兵喊:“太君,我的县大队裘世荣队长的干活……”他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证件朝鬼子哨兵晃了晃,“我们刚抓到一个女八路,要借用太君的电话向片山队长报告消息。”矮胖哨兵伸着短粗的脖子朝奶奶这边打量俄顷,咚咚咚地跑进了炮楼大门内。约莫一分钟哨兵又出来了,他身后一个挎着军刀的日本军官快步走到吊桥前往外仔细看了看,他显然是认出了裘世荣,阴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幺西,幺西,裘队长的干活,快快放下吊桥。”他对身旁的哨兵下令道。
奶奶踏上吊桥桥面时,心里就像揣了只兔子似的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毕竟是第一次深入到鬼子窝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一行人刚过吊桥,吊桥就又被吱嘎吱嘎地摇了起来。奶奶的心格登了一下,这回可是彻底断了后路背水一战啦.要么你死我活,要么我死你活。奶奶很快让自己镇静下来。进炮楼后,奶奶被从驴背上架了下来,裘世荣对着鬼子军官双腿啪地一碰行了个鞠躬礼:“太君,我奉片山队长之命,化装成八路工作队潜入到八斗碗村,将那里的土八路一网打尽。并活捉了这个女八路。”
鬼子军官眯睛死死地盯着奶奶。良久才开口:“幺西,幺西,女八路大大的漂亮。”语毕,他忽地从腰间抽出亮晃晃的马刀架在奶奶脖子上:“八格!你的就是那个骑在毛驴背上杀死皇军的小脚女八路?今天我要你死了死了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老村长攥着手雷绳索的手心都被汗水濡湿了。在这节骨眼上,裘世荣对着鬼子军官连连点头躬腰道:“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女八路是该死了死了的,不过片山队长说了要抓活的,他要亲眼看看小脚女八路长的啥模样。”
听了裘世荣的话,鬼子军官将马刀收回刀鞘。众人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惊魂未定的裘世荣不敢有丝毫怠慢,他见鬼子军官收起了军刀,赶忙趁势说道:“太君,鄙人想借用您的电话向片山队长报告一下情况,可以吗?”
军官的一双小眼睛快速转了转:“电话的可以用,不过你的必须向片山大佐报告说是在我的协助下抓到女八路的,我的话你的明白?”
“明白明白,鄙人完全明白。”裘世荣又是一连串点头。
“慢!”突然,鬼子军官挥了挥手对裘世荣说,“你的在向片山大佐报告之前,我的必须对这个女八路细细的检查检查。”
鬼子军官这一招把裘世荣吓得汗湿背脊:“太君,鄙人已经检查过了。”
“八格!你的检查大大的粗心,我的大大的信不过,我要亲自仔细的检查。”
裘世荣有些傻眼了,而此刻奶奶却出奇地镇静,她朝裘世荣使了个眼色,裘世荣立刻对军官说:“太君要亲自检查女八路大大的好,鄙人替太君解开她,好让太君检查。”说着裘世荣便动手为奶奶解开绳索。
鬼子军官的脸上露出了狰狞而淫邪的笑意:“幺西,幺西,裘大队长大大的会办事,我的会在片山大佐面前说你大大的好话。”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裘世荣边说边将解下的绳索扔在地上。鬼子军官追不及待地一把拽住奶奶的胳膊就往一旁的小屋里推去。奶奶给老村长使了个眼神。当奶奶被鬼子军官推进屋子关上房门的一刹那,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枪响刚落,老村长就霍地从衣袋中掏出一枚手雷高举手中厉声喝道:“都别动!哪个龟孙子敢动一动,老子就让他粉身碎骨!”趁着鬼子们惊愣的片刻。民兵们迅即冲向鬼子们搁枪的枪架、只眨眼功夫,十余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毫无防备的鬼子们,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械。突然,一名靠近炮楼楼梯边的鬼子猛地一个翻身上了楼梯,蹬蹬蹬地往二楼跑去,二层炮楼的射孔前还架着一挺机枪,那鬼子准是想抢过那挺机枪居高临下负隅顽抗。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砰地又是一声枪响,一只脚已跨上二层楼面的鬼子就像醉汉一般摇摇晃晃地往下退了两个阶梯,随即挺了挺身子一头从楼梯上栽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枪响的方向,大伙看到奶奶伫立在打开的门前,从容地吹着仍在冒烟的枪口,她身后直挺挺地躺着鬼子军官的尸体。就这样.奶奶和老村长这些“土八路”,凭着勇敢与机智端掉了鬼子的一个炮楼。
打那以后,尝够了奶奶和“土八路”厉害的片山队长再也不敢轻易下令扫荡和袭击八斗碗村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片山大佐在八路军举行的受降仪式上对八路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作为一名军人和山地作战专家,我的大大的不如中国一个裹小脚骑毛驴的花姑娘。惭愧惭愧!佩服佩服!”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这样回答片山:“请你记住,当一个民族连小脚女人也拿起武器反抗侵略时,这个民族注定是不可战胜的。”
奶奶后来嫁给了我的爷爷——八路军的一个干部。在生下我父亲的第二年,爷爷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奶奶从此再也没有嫁人。
也许是对侵略罪行的忏悔,也许是良知发现,片山回日本后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积极投身于反战同盟会的工作,还撰写回忆录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深刻揭露与反省。
也许是巧合,2010夏天,在世界夏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到来不久,奶奶以96岁的高龄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在奶奶的葬礼上,我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日本姑娘,她是片山大佐的曾孙女清川美树子,她是代表93岁行走不便的片山大佐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5周年有关纪念活动的。得知奶奶逝世的消息,他特地从北京赶到我家乡参加了奶奶的葬礼。她敬献的花圈上写着:“前事勿忘,后事之师,愿日中永不再战,世代友好。献给曾祖父心目中的英雄小脚奶奶——清川美树子敬挽。”那一刻,我突然悟彻了奶奶不愿提及当年往事的缘由——她老人家早已用那双握过枪的复仇之手轻轻地翻过了昨天的一页,连同那血与火的记忆——她希冀的是儿孙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杀戮、鲜血死亡阴影笼罩着的和平天空下。
我梦中的小脚奶奶啊。神勇睿智的奶奶,漂亮慈爱的奶奶。